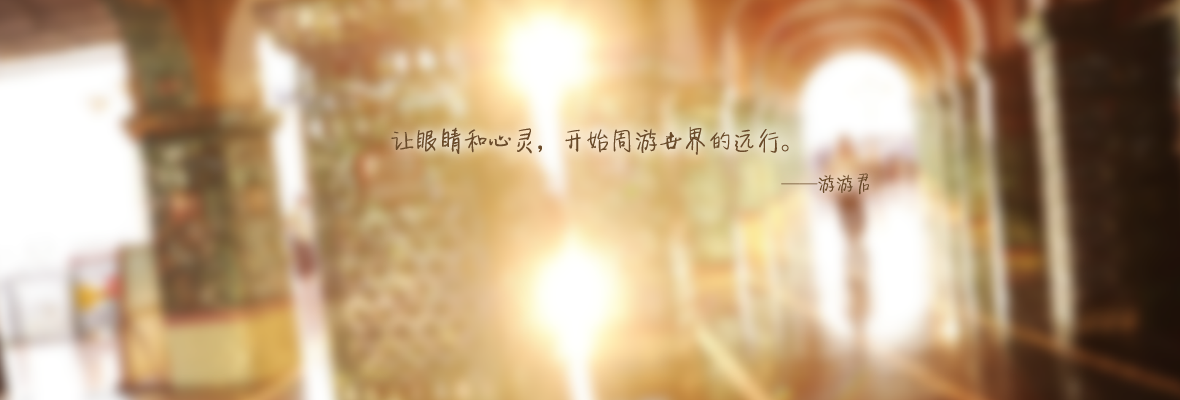
玩法:人文,穷游
发表于 2024-05-13 12:14
【黃劍博采風追影】【皇氏古建築大全】
Jumbo Heritage List © Epic Adventure of Jumbo Huang

无欺于死者,无负于生者,无愧于来者

第6142回:最狂的风最静的海,深闺禁苑梦锁界线

©原创图片(本图文中的图片版权归黃劍博采风追影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络Huang_Jumbo或JumboHeritageList),本章节图文中的图片具备一定的商业价值,

本图志全部图片谢绝一切非完整性的截图转载!请自重,特别谢绝各种手工特意叠加商业网站水印的转载!本作品保留一切权利。

作品中的文字不得直接或者间接用于以营利为目的一切商业行为,违者必究。本图文中部分章节文字内容可能局部来自公开网络或公有领域,仅供个人学习研究和欣赏而使用,文字没有明确商业用途。(©Image by Jumbo Huang, Part of Text citation resources was from public domain)

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感觉到了这个索维拉古城蓬勃的生命力。彩色拼接玻璃被小心翼翼镶进圆形窗户,缤纷炫目的色彩赋予了街头光鲜的生机,老旧的双开木门被漆上鲜艳的蓝绿色,各式花样多变的编织地毯吊挂在商铺门口。街上衣着鲜艳的当地小孩正在奔跑打闹,与背后的房屋完美相融,宛如一幅色彩浓烈的画。

我们经过一位摩洛哥群众推荐的当地餐厅,与不懂英语的餐厅侍应指手画脚了一番,他终于恍然大悟完美想尝试的正是餐厅里的招牌鸡肉塔基锅。

等待主菜期间,侍应们十分热心地端上了摩洛哥的特色薄荷茶,更贴心地比划着给我们介绍制作这些食物的食材和过程。

或许语言不通,但丝毫没有减少他们渴望给我们介绍当地北非民俗和美食特色的热情。相反,他们似乎花费了更多的心思来关切我们,担心因为自己的小小疏漏会造成我们这些异国人旅途的不快。

这些小的细节让我尤为感动。他们竭尽全力地向我们呈现索维拉的美,即便有着语言的阻碍,但每一个渺小的举动,都让彼此的世界更为相近。

等待了一会以后,煲仔饭塔基锅端了上桌,这是摩洛哥最有特色的料理。当地人用一种特制的圆锥形陶制器皿作为容器,铺上鸡肉、牛肉、羊肉或者海鲜,再放上胡萝卜、土豆、南瓜、蜜枣等配料以及各种摩洛哥香料,小火慢慢焖几个小时而成。

一个小小的陶器里蕴含了无比多元的味道,看似熟悉的食材,却被当地盛产的各类香料激发出全新的味道。深谙味觉规则的厨师,

醇熟地将各种食材扔进土制陶锅中,形成摩洛哥特有的菜系。煮熟后带锅直接上桌,开盖后看到炖肉溢出来的汤汁甚至让我们惊叹了一下。

还未入口,香气已经虏获了我们。混合着鸡肉,蒜蓉和当地香料等的香味,我盛了满满一勺塞入口中。

刚入口是鸟肉的清甜,伴随着各式配料及土豆的调和味道,咀嚼过后香料味溢出,浓烈又特殊。火候恰到好处,

柔软紧致的鸡肉沾上了酱汁令余香在口中久久残留,北非的鸡肉多是走地鸡,不像我以前在美国和新西兰吃的那种工厂饲养的机械化的傻鸡,它们缺乏运动,吃起来都没有肉的味道。

吃过饭后,太阳已经爬升到中正,走回夜宿的民居睡上一个回笼觉,下午走在被白人游客淹没的古城小巷,感觉每条街被我们踩烂了。这条街走过,那条街也走过了,熟悉那条小巷有着小资情调的咖啡馆,那条略微宽的街道有草编织的工艺品售卖。

索维拉老城是世界文化遗产,赭石色城堡,白色石灰墙,蓝色百叶窗,保留至今建于18世纪的斯卡拉堡垒,是精华所在。堡垒是防御工事,也是保护老城不受大西洋海浪冲击的城墙的一部分。它分上下两层,上层露台摆放炮台。登至炮台顶端,可远眺索维拉老城和一望无际的大西洋。海风吹拂,大西洋波涛汹涌,远望天际,心情豁然开朗,冤仇释怀。

如果拍日出就不要去斯卡拉堡垒,摄影师如果早晨去得太早,海边堡垒就没开放。值守人员通常8到9点以后来才过来开门。

有一次我竭尽所能,表达远道而来,时间有限,希望早些参观之意。无奈工作人员公事公办 ,委婉地拒绝了我的提议。站在路口台阶上观望的我,只好转身钻进鳞次栉比的摊位中等待。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又回到堡垒。此番路口锁链没有了,可以通行。
尽管在索维拉老城拍摄日出困难,但拍摄日落却是唾手可得,因为傍晚太阳是直接落到大西洋的,只要站在海边任何地方都可以拍摄到日落,但最佳拍摄地点显然是斯卡拉杜波特堡垒(skala du port)。

这座有四角燕子窝炮台的堡垒就在港湾边,能看到渔港和莫加多尔岛的秀美风光。从这里回望城墙围绕的老城,透过成群盘旋的海鸥,我眼中的风景与几乎所有官方宣传单上使用的动人照片别无二致。

在斯卡拉杜波特堡垒右侧有一个可以免费参观的博物馆,里面摆放着一些家具和马赛克壁画,上楼还可以参观一些木船的模型,到了傍晚之后,斯卡拉杜波特堡垒会在夕阳照耀下变成黄赭石色。

在四拱桥两侧都停泊着很多渔船,赭石色的斯卡拉杜波特堡垒已经不对游客开放,左侧新建的一个观景平台也不对游客开放,不过有一次我与一群洋人偷偷爬上去拍摄了几张照片。

在斯卡拉杜波特堡垒右侧有一段防波堤坝,只有约30到40厘米的宽度,所以走在水泥防波堤坝上是很容易摔到海里的,因为上面没有护栏,而且遇到狂风袭击时,如果两个人从相反方向走过去,在会面时会被风掀到海里。

我们第一次到防波堤坝上时,凑巧遇到一个本地人在岸边卖鱼,他会直接拿刀加工鱼,鱼的内脏会直接扔到乱石上,引来大量海鸟。
索维拉老城的日落每天都不一样,运气好能看到晚霞,每天傍晚,群众自发赶到广场以外的礁石边等待落日。绵延的岸边堤坝上已经聚集了大量前来观赏的本地人和游客。

没有喧闹的叫喊,没有急躁的起哄,所有人都静静观看着落日的金黄是如何一丝一点地消逝在海平面以下,仿佛对自然的变幻保有一种虔诚的敬畏之感,只是偶尔会遇到一些中外摄影团的游客拿着单反相机不停狂拍。

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美如画”的索维拉,原名莫加多尔,史料就有记载的古老城市,距离大不列颠群岛仅三小时的飞行,令这里成为欧洲人寻求海风迷恋浪漫阳光的胜地。
索维拉码头边呈长方形的建筑,有着厚实的砖墙、半圆形拱门、逐层挑出的门框装饰和交叉结构,具有典型的古罗马城市建筑风格。而临近城中,又林立了满是浮雕,精细又华美繁复的窗框,镶着贝壳等自然图像的圆柱的建筑群,葡萄牙,法国和柏柏尔风格的完美融合让人惊叹不已。

不是没有见过更绚烂夺目的日落,而是这一场日落平静地宣告了世间万物顺应规律作息的生态准则。朝代更迭,过客生死,唯一不变的是每天的日出和日落,这算得上迄今为止让我们我最为震撼的一场有仪式感的日落了。

我之前提到过手机基本上快淘汰掉单反相机了,但索维拉却是一个很容易看到游客使用单反相机的地方,因为只有真正喜欢摄影的人才会来索维拉,而在摩洛哥其它地方则罕有使用单反相机的人。

而且更意外的是,我傍晚还遇到一个使用莱卡相机的富人,他穿着白色长裤和黑色上衣,斜跨一个小包,脚穿休闲的拖鞋,他站在海边拍了几张照片就离开了,他不会像那些挂着单反相机的摄影师像打机关枪一样不拍个上千张照片不愿意罢休。

两个年轻的欧洲夫妇也站在我旁边拍摄日落,当人群渐渐散去时,我们又见证了漂亮的晚霞。

晚上的古城更有物色,我们会参观一些老式的民居,有些被改造成酒店,可以免费参观,在如此繁复奢华的禁苑里,一方质朴简陋的天台却成了女眷们的天堂,她们在夕阳最美的傍晚和邻家的少年暗送秋波,也在天台上晒制风干天然花草植物酿造的护肤品。而这里的一座座里亚德就是女人们的深闺禁苑。

里亚德是摩洛哥最传统的民居,是有中心花园的“回”字型的庭院建筑。一般都是三层的高度,除了一个不显然的入门外,三层建筑里面所有门窗都是朝内开的,这种建筑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穆寺林女性隐私的需要。

里亚德一般为两三层楼高(Riad),是欧洲建筑杂志最常见的主题之一,不少的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前仆后继奔赴摩洛哥抢购年老失修的里亚德,在马拉喀什和菲斯就有许多被整修为家庭旅馆的里亚德,本次旅程,让游客做个天方夜谭的梦。
我们走在石板路上,经过清真寺和

香料市场,终于找到一家餐厅,我们走进去吃晚餐。

索维拉没有太多正式的景点,却是个闲逛的好地方。老城、市集、城墙、港口和海滩都很适合慢悠悠地探索,中间穿插放松的午餐和悠闲的薄荷茶休息时间。

索维拉筑有城墙的老城建于18世纪末,在2001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是北非地区杰出且保存完好的欧洲军事建筑典范。对游客而言,狭窄的街道、市集、街头小贩、葱翠的广场和拥有华丽木门的白房子让漫步老城充满乐趣。

在索维拉看狂风吹拂的大海,我总会想起顾城。

世界和我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看上去是彼此融合的,但其实,世界在“我”眼中,是如此独立,似乎“我”并非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乃是“我”的观察所得。

最狂的风,最静的海,也就是“我”需要一个最坚实的基础,与一个最自由的灵魂。
2017年我有幸数次拜访新西兰海岛上的顾成故居,那是顾成拿斧头砍杀妻子的阴宅,一直罕有人光顾;

有时,很长的心绪,往往只需要很短的释放。
心绪很长,会形成一种积累,这种积累若能得到一种肆意的喷发,会比它缓慢被蒸发更有意义。
比如我们不爱一个人了,或许早就有“预谋”,但真正的“断根”,可能就在某一瞬间,因为某件小事。
顾城的短诗,几乎都具有这种魅力:用最短的文字,抒写最长的领悟。

我听说汉诺也曾经造访过索维拉,航海家汉诺是一个约公元前五到六世纪的迦太基探险家,闻名于他沿非洲西海岸的海上探索,然而只有希腊版的汉诺手记记载了他的旅程。
今人研究其航线,认为他可能曾到达加蓬。航海家汉诺可能生于约公元前570年,卒于约公元前450年,虽然一些古典主乂者认为他的生卒年不会比公元前633年和公元前530年更近。

迦太基曾任命汉诺率领约有六十艘船的舰队在非洲西北海岸探险与殖民。他驶过直布罗陀海峡,沿海今日摩洛哥的非洲海岸建立或重建了七个殖民地,并沿着非洲大西洋海岸探索更远。一路上汉诺遇到了各地土著并受到他们欢迎。

在汉诺旅途终站,他发现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岛屿,他描述岛民野蛮而多毛,虽然尝试捕获当地男人但失败并以带走三个女人告终,然而她们凶猛得汉诺不得不杀死她们,只能将人皮带回迦太基。这些人皮在汉诺返家后存于朱诺神庙(塔尼特或阿斯塔蒂)。

据老普林尼所说,这些人皮幸存直到罗马人毁城,在汉诺远征三百五十年后仍完好。跟随汉诺旅行的口译员称这些人为Gorillai。十九世纪美国医师兼传教士托马斯萨维奇与博物学家杰弗里·怀曼初次描述大猩猩时采用了衍生自上述蛮族的单词gorillas。

汉诺说,“在其最深处的陷坑类似我们之前描述过的岛屿,里面像是个湖中岛。岛民都很野蛮,阴盛阳衰,皮肤粗糙:我们将之称为Gorillae。我们试图带走一些男人但是失败,他们都轻易逃到悬崖顶,然后向我们掷石;

我们带走了三个女人,但她们一直凶狠反抗,对捕捉人又撕又咬,我们迫不得已杀死了她们,剥下人皮带回迦太基;我们的粮食不够继续下去了。”
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可能曾就汉诺原报告写出以下故事:

迦太基人告诉我们,他们曾与越过赫拉克勒斯之柱生活在利比亚一部分的人交易。抵达此国后,他们先在海滩上将卸下的货物整齐放好再回到船上点烟。见烟的土著会在地上放下一定数量的黄金来换取货物,然后离开一段距离。
迦太基人再次上岸,如果他们觉得价格合宜便会拿走黄金离开,否则就会回船等待土著加码,直到双方满意为止。双方都十分诚实,迦太基人在认为价格足够前从来不碰黄金,而土著在黄金被带走前也不会触碰货物。

阿里安曾在其亚历山大远征第八卷末提到汉诺远征:
此外,利比亚人汉诺曾由迦太基出发越过赫拉克勒斯之柱来到外海,再由利比亚的码头一直向东航行了三十五日。

此间他陷于无尽艰困、淡水匮乏、酷热、还有流入大海的火热溪流。据老普林尼言,汉诺在同为迦太基航海家的希弥歌探索欧洲大西洋海岸时开展旅程。老普林尼写道他由加的斯到阿拉伯环非洲绕圈。

晚上回家阅读了《禁苑•梦》的一些片段,感慨良多。
那奔驰的想象力源自深闺禁苑的封锁本质。
如果你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打开百叶窗也无用。所有的穆寺林国家的窗子都朝向院子,没有一扇是向外开的。
《禁苑•梦》,有关界线——男女之间,深宫内外,老城新城,夙愿规矩。

法蒂玛的外祖父有八个妻子,她父亲只有一个妻子,但却和哥哥全家同住。对于书中的“我”(法蒂玛)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来说,成人世界里有那么多的东西无法理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一举一动,仿佛都有新旧两种势力在角力:面纱和小头巾、薄荷茶和口香糖、奶奶们绣的非斯传统图案和堂姐绣的怪鸟,如果你觉得生活缺少趣味,只要摆上茶点,抛出其中随便一个话题。
人们游走于种种墙之间讨生活,触犯者也肯定不如遵守者过得容易,就像我们住的胡同,墙就是界线,想要突破界线的,不是小偷就是撞南墙的笨蛋。同样,界线也有各种各样,但正如书中女仆珉娜说的“不论什么界线,总是一边是强者,一边是弱者”。她小时被人拐卖,曾被吊着放进井里,脚下就是满是蛇和虫子的凉水。

经年累月的时间过去,古老的世界和无法打破的界线早已化为乌有。层层叠叠的厚重棉质面纱被撕裂,深深根植入地下,紧紧攥着泥土,腐烂,腐烂。有风的时候,扬起一些脂粉和泥土混杂的气味,是魂灵不灭的味道。

世界上有很多种的墙。有的又高又坚固,抬头都看不见边;有的上面还竖着插着玻璃茬儿,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有的年久失修,斑斑驳驳,长满青苔和爬山虎;有的仅仅是不到一人高的篱笆,两边的人扒着它聊着天;甚至在那令人肃然起敬的上古年代,讲究画地为牢,地上划个圈,比现在有的墙还管用。

作者法蒂玛用风趣而真实的笔触记下了十岁之前对深闺禁苑的回忆。那是在非斯,华丽庭院由马赛克瓷砖、喷泉、镜子、长廊、完全对称的造型组成,只有一方天空象征着外部世界,所有的窗户都向花园内廊,没有一扇窗是向大街的。

孩子们每天晚上要一一吻过长辈的手,甚至屡屡被自己绊倒,惹人嬉笑,只为了尽快奔到平台上去听迷人的故事,深闺女眷们才能绘声绘色讲述的故事。偏偏是在如此繁复奢华的禁苑里,一方质朴简陋的平台却成了女眷们的天堂。像一千零一夜里的山鲁佐德那样讲无穷无尽的故事,上演自导自演的戏剧,在夕阳最美的傍晚和邻家的少年暗送秋波,也在平台上晒制风干天然花草植物酿造的护肤品。

我印象最深刻的摩洛哥,是在梅艳芳的一部电影里。身患重病的寂寞太太明知丈夫有外遇,便独自出游,在堪称艳丽的夕阳中,她与新结识的女子一见如故,同住一间房。结果,那女子竟然就是丈夫外遇的对象……当时,是背景里的浓烈的华丽、女人的心如刀割让我难忘。
其实就在几十年前,摩洛哥的伊寺兰教民中还保存着根深蒂固的一夫多妻传统。女眷守在家宅后宫中,越是社会地位高的富庶人家,越是严格地遵守禁苑陈规。或许,把两个现代香港女子惺惺相惜的故事放在摩洛哥背景里,真是很有寓意的吧。

坚持在平台上、月光下的浪漫聚首,让心爱的人敢于忘掉其社会羁绊,哪怕只是一个夜晚,完全放松,干点傻事,握着你的手看星星,我想这可能就是为幸福培育肌肉的一种途径,而当笑声与春风交融时打造如此温柔的夜晚可以算是另一种。
但这种迷人的夜晚很少有,或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白天生活极为呆板,处处戒律。梅尔尼斯家明令禁止蹦蹦跳跳或嬉笑玩闹,那一切只有在隐秘的时刻和地点才会发生,例如在下午男人们外出后的院子里,或晚间空旷的平台上。

树立一个孩子的坚强个性有多种办法。其中之一是增强他对别人的责任心。仅仅是咄咄逼人,当邻人干了蠢事便扑过去掐他或捏她的喉咙,这是一种解决办法,但这肯定不是最优雅的。如果你鼓励她对同院更小的孩子负起责任,这时你也就给了她增强意志力的机会。指望萨米尔的保护亦无妨,条件是她要学会保护别人,她也就会用同样的技巧来保护自己。

女人和女人之间也在刺绣、头饰等细节上争论不休,传统派恪尽职守维护的传统不外乎是古老的图案、沉默顺服的个性,祖母沉重服饰下的沉默意味着尊严和权利。但现代派却向往女性男性真正平等的一天,世界已然向她们打开,她们知道法国女子风情万种的装束、化妆品、夜生活,知道女奴和公主的故事,妈妈大胆地率先使用透明的小面纱,甚至会想出到河里比赛洗涤巨大餐具的娱乐项目!

服从。尚还久远的年代,蓝白相间的陶瓷地砖、雕花木门、织棉透花窗帘、镀银栅栏、彩色玻璃拱顶的对称式四方院落,将城里足够多具备小才小貌小气质的女子汇集,组成神秘且极度规矩的大家庭。容貌家世虽有不同,却都情愿不情愿地恪守阿拉伯世界男尊女卑的潜规则

滋养。如鱼得水的是男子。就算相貌并不出众,但只需要有些权势,便能在身边换上几轮曼妙的女子,生养一群得到真主庇护的孩子。无需赴汤蹈火。将女子与街上的陌生男子隔开,仅是男子们维护自身和家族名誉的低劣把戏。

迁徒。终究是恶劣的行径。那些在女子间流传的抗争故事,能改变的只是少数人的信仰,终究无法根深蒂固。在熟悉的院落年复一年挣扎,假想是从未曾到过的陌生城市。于自欺欺人地幻觉里流放出新的地域和新的等待,低廉地成为为脆弱而无助的心培育肌肉的一种途径。

殖民。统管杀戮之间。狭窄阴暗的街道一直延伸下去,向着笔直的新街。驴马换成汽车,每天早上醒来时罪恶的负感撕开干燥幽黄的肌肤,遭遇突如其来的低垂区间,体验一片前所未有的混淆地带。殖民者也是充满恐惧的,闯入蜿蜒曲折的巷子便再也无法找到归路。

爱情。是幻术。来自麻痹和愉悦。热烈的交换情感与身体,是超越神明所能允许的范畴,被禁止。历史的脆弱性,也便如此罢了。“幸福是给予和获取之间的平衡”,仅是无法实现的夙愿(路佳瑄)。

《禁苑·梦》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手法,展示了一幅上世纪中叶摩洛哥妇女的生活画卷。小说讲述了一个出生在摩洛哥非斯老城的女孩,从小被教育如何识别“界线”并尊重“界线”,这“界线”即指男女的界线、深宫内外的界线、老城新城的界线、愿望与规矩的界线。然而女孩却企图用她好奇的眼睛与纯真的心去打破这些界线。

作者塑造了能背诵《一千零一夜》的哈比芭、全副武装却又戴满首饰的达慕、叛逆的莎玛、贫穷的珉娜等人物,用细致入微的笔触描摹了很多女子的日常生活、梦想、现实冲突及抗争,真切而又不无幽默地表现了阿拉伯世界女性对自我的认知与追求,同时展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从摩洛哥精神首都非斯老城到广阔农村的生活场景。

法蒂玛·梅尔尼斯1940年出生于摩洛哥的精神首都非斯。少年时代进入摩洛哥首批男女生混合的私立学校学习,后留学法国和美国,继而成为拉巴特穆汉默德五世大学科学研究院教授、联合国大学委员会成员。《禁苑·梦》是梅尔尼斯撰写的第一部文学作品,1994年在纽约出版后反响强烈。

第6143回:陀螺式死循环内卷,间隔年被时间鞭策
推荐相关游记更多
更多相关问答
-
#青岛村尚春宿设计师酒店#真的和图片一样吗?摩洛哥大床房是两个独立的卧室吗
2025-07-23 1回答 -
#敦煌大漠行者沙漠露营基地#我定的摩洛哥帐篷付费可以升级这个带独立卫浴的太空舱吗
2025-07-12 1回答 -
#敦煌鸣沙山星野沙漠露营星空酒店#4月初住摩洛哥帐篷会冷吗?
2025-03-30 1回答


评论